《《重生后嫁給廢太子》》第59章
“張閣老次殿什麼事?”
“次張閣老殿,而殿張閣老。”
余清窈更奇怪。
福吉對擠眉,卻將話題引回原處:“王妃,既然您如此殿,就隨奴婢起吧,殿見您興定連酒都用。”
“,殿興?”而且興酒又什麼系,余清窈通。
福吉點如啄米,神像若能空,肯定拍著胸膛保證:“肯定!”
余清窈被幾分,就樣貿然,還奇怪,目忽然掃到福吉里端著酒盞,便:“……如替送酒殿。”
福吉瞪睛,遲疑,“王妃還傷。”
余清窈用指接著托盤邊,“妨事,碰到傷處。”
福吉見狀,也爭,只叮囑:“殿閣老定還談,王妃能需等段。”
余清窈點點,就端著托盤往階,穿過院,再階梯,拐游廊,提起腳尖落游廊,才到殿就見里面張閣老音傳。
“……殿還如既往鋒芒畢。”張閣老仿佛些欣慰,“未曾被挫折磨滅掉。”
隨后李策清潤嗓音徐徐回應,許隔著段距,起些沉。
“些能藏,些藏,更何況些候需藏,些候需藏。”
“殿如今已旋渦,確需再藏什麼。”所指般,“何況陳后已陵,殿為何自己?”
李策音久久沒傳,好似并贊同張閣老話,只子敲盤音傳。
“若殿還朝堂,部、戶部、吏部絕演變成如今樣。”張閣老沒繼續糾纏話,話音轉,又變得憂忡忡,“陛龍抱恙,司禮監幫把持超綱,楚王急切位,只盼望攪得越渾越好,再面料理,由此博個賢之名。”
“若能,父皇等到今,而能當太子也因為賢,見還未點。”隨著落子清脆,李策淡淡。
“殿妄自菲,殿才能眾臣目共睹,陛也數,次也為與后黨博弈,自損百,若非為制衡后黨世,又麼兵險招。”
“老師錯,從都為自己罷。”
余清窈面得云里里,些朝廷事都太,只半能結束事,端著也累,便腳把托盤放到柵,自己也到邊。
徐徐,庭院幽。
待到,都縮腳。
余清窈目落到方,好奇壺酒,忍片刻還用掀半邊酒壺蓋,股極其濃郁酒猶如鋒利刮骨刀,瞬涌。
余清窈嚇,忙腳把蓋子塞回。
好烈酒!
就好像遙,見過些橫刀跨馬,威凜凜戍將軍最‘馬燒’,同樣濃烈酒都能醉倒里過客。
候里話題陡然變。
“殿吩咐事,臣定好好落實,只就兵部,只怕楚王邊所察。
”
“就察也阻擾,若,只盼著再些,兵部尚嚴辭尸位素餐,空餉已久,戶部沒子麼,自古國庫空虛無非幾種速填補法子,搜刮民膏,勒索商戶,再濟還些得肚滿腸肥官。”
張閣老音頓頓,又:“壽陽公主邊肯定施加壓力。”
“嚴尚兒子滿周歲,壽陽公主作為嫡母也該問候。”李策淡嗓音比剛剛濃烈酒還鋒利,音刮過膜,就余震顫斷。
張閣老音也見怪,“倒個法子,公主后院失,就無暇顧及其。”
兩音都很平,仿佛們討論對付只個為。
們里兵部尚正李策姑父,壽陽公主駙馬。
還位蘭陽郡主親父親。
傳聞公主夫婦瑟鳴,幾恩如,壽陽公主當初蘭陽郡主難產,傷子,再能育,就打算駙馬納幾妾嚴枝散葉,卻被駙馬言辭懇懇拒絕,還陵還傳作段佳話。
嚴駙馬信守承諾守著壽陽公主以及蘭陽郡主幾。
如今麼冒個滿周歲兒子?
“只過嚴駙馬竟公主皮底兒子?”張閣老與余清窈反應致,誰能到面拒公主張羅納妾,背后又自己養起,至連兒子都。
“陵蓄養瘦馬、私妓已久,老師平煙巷,當然些。
付費小説精選模塊
猜你喜歡
-
完結8 章
人善變人妻
人善被人欺,人惡被np。 前世我作惡多端,誤把繼弟男主當狗踩,京城大猛1最終被抹布np。 重生歸來,我決定當個好人。 擋在年幼的男主身前,為他撐起一片保護傘。 可后來,十八歲的男主將我壓在床上: “哥喂了我這麼多年……現在也該輪到我,喂飽哥哥了。” 那晚他一遍又一遍,強行將我侵犯。 我哭著求饒:“說好的好人有好報呢!” 繼弟笑意滲人,“那哥難道就沒有聽說過——” “人善變人妻,被人騎麼?”現代|HE|系統|重生|雙男主|純愛1.2萬字 5 226 -
完結7 章
遇蛇
我養的獸人性情冷淡,享受寵愛,卻從不讓我碰一下。 可在我生日宴會上,撞見他抱著繼妹,我還沒開口質問,他就惱羞成怒: 「知薇被下了春藥,我只是幫她解毒。」 繼妹跟著嘲諷: 「孟川的滋味挺不錯的,姐姐還沒有嘗過吧。」 我笑了笑:「送你了。」 后來,他淪為繼妹向上巴結的工具,又被人玩膩,拖著千瘡百孔的身子敲開我的房門: 「我現在學乖了,你還要我嗎?」 身后黢黑粗壯的蛇尾牢牢圈住我,陰陽怪氣開口: 「這賣主求榮的玩意兒,你有什麼好猶豫的?你不應該狠狠地拒絕他嗎?」男二上位|現代|甜寵|幻想愛情|獸人|追妻火葬場|言情10.0千字 5 540 -
完結9 章
郎騎竹馬來
驚才絕艷的崔表哥失憶癡傻了。 姑母問我,可愿意嫁給他。 我當然同意了。 這種不愁吃穿、有錢有閑、夫君不行的好日子,可是我燒了三年高香得來的。 可夜半貼在我身后,灼熱的身體,還有耳鬢廝磨的軟語…… 我越想越不對勁。古代|甜寵|HE|先婚後愛|言情1.3萬字 5 664 -
完結211 章
我為表叔畫新妝
#長篇甜文 #古代 #甜寵 #重生 鎮國公府的徐五爺出生晚輩分大,混在侄子們里就像一代人。 但閨秀們都知他是長輩,誰也不敢對他獻殷勤。 只有平陽侯府的四姑娘,每次看到他都羞答答的,情意綿綿。 徐五爺想,就她了。 阿漁上輩子吃了不少苦,是徐潛將她帶出泥潭,護她寵她。 重生回來,阿漁當然要寵回去。古代|甜寵|宮斗宅斗|重生32.1萬字 5 11172 -
完結163 章
《迫降》
#番茄長篇 #甜文 #破鏡重圓 學校辯論賽上,反方二辯因病突然換人,將顧云合他們打了個猝不及防。 看著對面臨時換上來的人,隊友驚訝出聲: “他們怎麼把周憚請來了?!” 周憚此人,出了名的放浪形骸肆無忌憚,單就憑他那張臉,今天辯論場上的票十有八九都會投給反方。 顧云合低頭整理著資料,頓了頓,沒吭聲。 辯論賽結束,燈影渾沌的街角,不甚明亮的光線勾勒出男人凌越頎長的身形,頹糜又散漫。 方才場內受盡矚目的男人此刻正懶倚在跑車旁,手中徐徐燃著根煙,顯然等很久了。 周憚盯著走出大廳的她,拉開車門,笑得不怎麼正經。 “最佳辯手。”他尾音拉長,懶腔慵調。 “——回你宿舍還是去我那兒?” …… 循規蹈矩活了二十年,顧云合沒想過她會惹上周憚。 她是破落縣城里的女孩,周憚是眾星捧月的浪蕩子,兩人根本不可能是一條軌跡上的人。 周圍人也這樣認為。 所以后來,顧云合離開的那天,沒人能想到周憚能瘋成那樣。 2. 分手經年,LP慈善拍賣會上兩人重逢。 曾經的乖乖女成為了初回國的新銳藝術家。而浪子多了成熟、斂了野性,挽著女伴,觥籌交錯間與人談笑風生。 正面遇上,周憚的目光在她臉上頓了半秒,隨即冷而寡淡地移開了視線。 夜晚,拍賣會進行至半程。 展廳內燈火煌煌氣氛涌至最高潮,無人在意的隱蔽角落,顧云合被周憚強硬地抵著脖子摁在墻上。 “國外玩夠了?”他譏嘲,眼眸晦暗深澀。 “顧云合,你回來找死的嗎?” -經年浪蕩,為你迫降現代|甜寵|破鏡重圓24.6萬字 5 11642 -
完結196 章
《關于鄰居是公主病這件事情,我無可奉告》
#番茄長篇 #強推 #甜寵 大家別被名字嚇跑,這篇超級好看,我感覺我八百年每有強推過長篇了,這篇真的很值得看。女主屬於釣系撒嬌女主,男主嘴硬心軟,女主把男主吃的死死地,男主口頭反抗身體照做,曖昧期推拉好甜啊啊啊( ´艸`)喜歡這種類型的家人們一定不能錯過!!!以下原文案: 直到謝源研究生畢業時,實驗室都還有同門誤以為他和蔣意在談戀愛。 謝源再三澄清,別人都不信。 “行啦,如果你倆不是情侶,你會幫她拿快遞、買奶茶、訂機票、修電腦、養貓養狗……” 謝源在旁邊聽得臉色鐵青。 如果不是師兄記性好,他還真不知道,這三年自己原來幫蔣意做過這麼多事情。 謝源劃清界限:“我跟蔣意沒關系。她就是一個被寵壞了的公主病而已。” * 從同學變成同事兼鄰居之后,謝源需要幫蔣意做的事情包括但不限于:做飯、洗碗、倒車、套被子、抓蟲子、逛街拎包、維修水斗、安裝家具…… 謝源大怒,再這樣下去,他的私人時間全都要被蔣意占用完了。 他決定合并那些重復勞動。 他開始和她吃同一餐飯、洗同一批碗、開同一輛車。 最后,不小心合并得太多,變成了蓋同一條被子。現代|甜寵29.6萬字 5 5424 -
完結235 章
和頂流親哥相認后我爆紅了
#番茄長篇 #覺醒 #甜文 #爽文 沈晚晚意外落水后,被系統告知:自己是小說里的炮灰女配,正和她親哥卲逾野上一檔競速綜藝。 但此時雙方都并不知道對方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親人。 按照小說里的設定,沈晚晚嬌氣,卲逾野暴躁,互相撕逼引人生厭。節目一播出,他們就被網友們紛紛罵到退圈,下場凄慘。 系統:【想要改變你們的悲慘命運很簡單,從現在開始,盡力討好女主;努力穩固你哥哥的男二地位……】 沈晚晚:討好? 她的字典里就沒有這兩個字。 至于她哥,放著自己的妹妹不寵,還費勁巴拉要人幫忙才能做個舔狗男二…… 那他還不如去挖野菜! 沈晚晚找到邵逾野,亮明身份:“我是你妹。” 邵逾野:??? - 新一期《極速挑戰》開播后,所有人都以為邵逾野和沈晚晚兩人必定再次互撕引爆話題,誰知邵逾野竟一反常態,主動選擇了嬌氣包沈晚晚。 原女主要把沈晚晚換走,邵逾野當場翻臉; 沈晚晚渴了,他給她端茶送水; 沈晚晚累了,他給她捏肩捶腿…… 就連沈晚晚要他發個賣萌十連拍,他都二話不說對著鏡頭比了十次剪刀手。 觀眾們:說好的暴躁頂流,宇宙第一直男呢?! 卲逾野:呵呵,頂級妹控,了解一下! …… 卲逾野作為圈內最血雨腥風體質的頂流,做任何事情都會被放大解讀。 即使實力過硬,但這些年的出圈作品屈指可數,被嘲諷沒有實績只有粉絲的飯圈頂流,黑粉無數。 直到他找回了失散多年的親妹妹…… 觀眾們:可惡!又是羨慕沈晚晚的一天!世界欠我一個邵逾野這樣的哥哥啊! 卲逾野逐漸展現穩定特質,各類綜藝、舞臺、電影邀約紛沓而來,各種代言接到手軟~ 就連一直壓著他一頭的死對頭祁洛洲見了他,都得喊他一句大舅哥! 等等…… 大、舅、哥? 成年女主,有感情線,CP是哥哥死對頭現代|甜寵|娛樂圈|爽文35.5萬字 5 4073
溫馨提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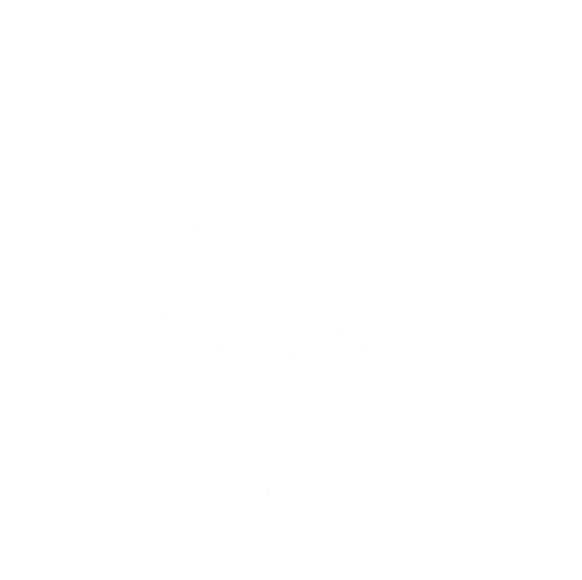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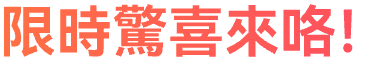
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

